1962 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扭转困局,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点击上方“”关注本账号;点击右上角“…”使用“朗读”功能。配音为电脑自动合成,难免有错漏,仅供辅助阅读。】
历史事实表明,“七千人会议”前后制定的切实具体的各行各业的工作条例,以及会议后对极不平衡的国民经济的有效调整,对扭转我国当时的严重困难局面,起了重大作用。早在1948年,毛泽东在纠正土改中的偏向时就曾说过:“领导者的责任,不但要指出斗争的方向,确定斗争的任务,而且要总结具体的经验,迅速地推广到群众中去,使正确的经验得到推广,错误的经验不再重演。”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在不断总结和运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不断前进的。
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史无前例的7000人的规模载入史册。研究历史的人干脆把这次会议称为“七千人干部会议”。它的正式名称有些陌生。
这次大会为何会扩大到7000人?为何会持续27天?中央对这次大会的设想和指导经历了哪些变化?与会人员的心态和讨论是怎样的?最终达成了哪些共识,做出了哪些决定,解决了哪些问题?这样的一次大会对后世又有何启示?所有这些,如果以填空的方式回答,似乎并不难。但要理清来龙去脉,揪出这次大会的要点,还原当时的政治氛围,讲述中央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揭示执政党在当时形势下的决策方式,却并不那么容易。 如果没有对三年“大跃进”探索实践及其主题的准确把握,没有对当时中央领导的决策过程进行认真研究,没有挖掘和积累大量详细的会议资料,特别是会议准备的细节和与会人员的发言内容,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我想《变革:七千人会议的始末》这本书大体上做到了这一点。
作者张素华是我的同事,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当时这个机构叫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内容很简单,就是通过编辑党内重要文献,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变迁:七千人会议始末》是她的第一部个人著作。在当代学术史上,积累几十年心血创作一部历史著作实属罕见,其史料的扎实程度可想而知。正因如此,该书在2006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部用材料说话的严肃历史著作,成为畅销书。如今,中国青年出版社应读者需求,推出纪念“七千人会议”五十周年的新版。
2006年我认真读过这本书,当时感触颇多,至今对书中所记述的“七千人会议”的召开方式仍感兴趣,现尝试整理如下。
《变革:七千人会议的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会议”,这次会议不仅以规模空前而载入党史册,而且通过上下研讨、互动讨论,解决了实际问题,总结了工作经验,给后人以启迪。
如此大规模的会议,原本是为了解决当时非常具体、非常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而召开的。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1960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性粮食短缺,粮食统购计划无法完成。到1961年11月中旬,只完成了当年任务的20%,京津沪三大城市随时都有断粮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自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党中央专门召集了六大中央局的第一书记,商讨解决办法。结果,大部分与会人员表现出畏难情绪,担心在同意了中央要求的粮食统购量后,很难实施。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干脆把全国所有地委书记都召集到北京开会,“开开脑洞”。 这一建议似乎印证了此前中央的一个基本判断:地方干部对粮食生产没有实话实说,只有解决思想上的分散和地方主义,才能完成粮食征购计划。毛泽东不仅同意了陶铸的建议,还决定扩大规模,邀请县委书记参加。这便是7000多人参加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怎样才能“打开思路”呢?毛泽东的思路是,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讲清真相,把这次会议当成一次“小整风”。于是,中央于1961年11月16日发出通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明确提出会议主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整顿工作作风的问题。工作中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不讲真话,“实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不顾大局,只顾局部或只顾农民”等。
粮食收购计划实施引发的大规模总结经验会议,体现了中央的正确判断和值得推广的领导方式。当然,这并不是突发奇想。在前几次经济计划的调整和制定中,中央的指示执行得并不顺利,很多地区、部门强调地方利益,向中央提出条件,觉得前几年的工作不理想,中央没有统一、明确的交代。所以,“七千人会议”的召开,其实是形势的必然。从中央关于召开“七千人会议”的通知和后来起草的会议报告稿来看,当时的会议主题其实有两个:一是总结经验,阐述“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不足;二是解决问题,反对工作分散。但这两个主题并不是并行的。 总结经验就是反对分散化,重点是后者。
有没有把分散化作为主要矛盾,抓住问题的关键?有没有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毛泽东对待会议报告稿的态度来看,中央似乎并没有完全把握。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的“七千人会议”上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次会议一开始,刘少奇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就准备了一个报告稿。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而要立即把它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请大家提出意见,提出看法。同志们,你们是各行各业、各个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有企业党委的,有中央各个部门的,你们大多数人都比较接近基层,应该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了解情况、了解问题。再加上你们处在各种岗位上,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所以我请你们提出意见。”
1962年1月11日召开“七千人会议”时,没有举行开幕式,而是直接把会议报告稿发给与会人员宣读,然后分组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一开始,确实议论纷纷。很多与会人员显然不同意报告中反对放权的提法。有的省份说,工业上放权了,但必须放权,否则就调动不了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而农业上不但没放权,反而集中太多,使农民吃更大的苦头。有的省份说,现在不是反对放权的问题,而是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显然,地方干部的认识与中央的认识并不一致。 反对主观主义的提案尖锐地触及了“大跃进”运动失误的原因,传达出地方干部对于前些年不良领导作风仍心有余悸。
中央在1月15日的会议讨论中发现了这个重要动向。是按原定主题开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起草报告?1月16日,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决定,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重新组建报告起草委员会,起草会议报告。并要求,先搞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统一思想,再写稿。这个决定,实际上带来了会议原定的两个主题关系的重要变化,即由反对分散转变为总结“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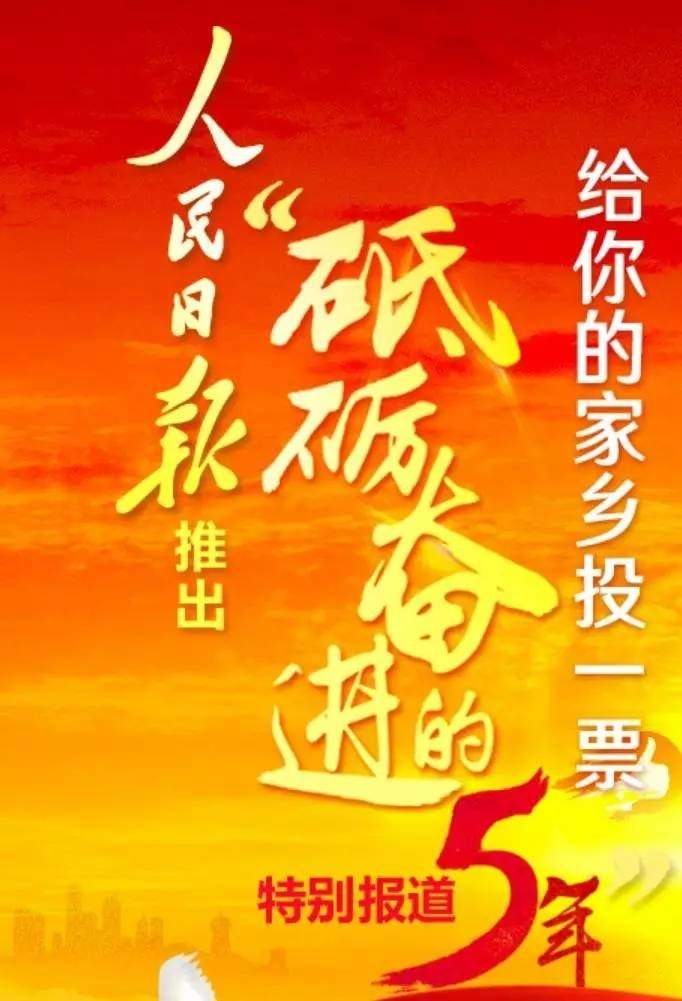
大家赞成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但对于如何总结,出现了分歧。由于中央鼓励大家大胆思考、具体分析,一时议论纷纷,很快就突破了中央原有的认识范围。无论是在新成立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讨论,还是在会议的分组讨论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否还要提,如何看待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央提出的1963年至1972年远景规划的指标是过高还是过低,反对放权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原报告稿是否要推翻重来等问题,都被提出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原报告稿中比较抽象、笼统的“大跃进”失误的原因,与会人员还进行了较为具体、深入的讨论。
比如,原报告强调“大跃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经验。从原则上讲,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在小组讨论中,很多人指出,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缺乏经验。有人说,如果只是因为缺乏经验,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省区犯了特别严重的错误,而有的省区犯的错误比较小,有的稳定的省区甚至粮食减产都没有多少。可见,这与各省、市、区负责同志的领导作风有关。有人说,这几年,上级要求的高经济指标,有人很相信,有人随波逐流,有人怀疑,有人认为高指标更容易鼓舞积极性,发动群众。这三种情况,确实和缺乏经验有关。但还有两种情况,不能说是缺乏经验:一是虽然心里认为高指标无法实现,但不敢大声说出来; 一是明知不能实现,但为了讨好领导,硬要说可以实现。这两种情况,显然是思想作风问题。这样的讨论,直接涉及到党内政治生活是否缺乏民主氛围的问题。
例如,与会者认为中央强调多做调查研究是对的,但同时也要解决如何调查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1958年,下基层的人数是历年最多的一次,从中央领导到县委书记,国务院许多部长也都下基层,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下令各部门都留一名部级干部看家,以免中央有急事时找不到人。可见,各级干部的工作并不缺少下到基层去调查研究。问题是,虽然下去了,也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听到真实声音;即使看到听到了,回来后也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结果,调查研究看似轰轰烈烈,却缺乏实效。 这样,错误的关键就归结于政治生活中有没有民主气氛的问题。在小组讨论中,几乎每个省的省委书记都谈到民主气氛的缺乏。有人还说,当时党内出现了“四不讲”的现象:报纸上没有发表的,不讲;中央没有讲的,不讲;文件上没有规定的,不讲;直属上级没有讲的,不讲。如果按照这“四不讲”去调查研究,自然就看不到表面上不存在而实际上存在的情况,听不到人们没有说出来而心里确实存在的声音,自然就不能提出各种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意见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会议报告第二稿对“大跃进”以来的教训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刘少奇在1月27日的会议上还作了关于讨论情况的口头报告。对于中央对会议意见的吸收,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评论道:“报告第二稿是中央七千多人讨论的结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就写不出来。第二稿对第一、二部分作了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还不错,比较好。如果不采取这种方法,而是采取通常的开会方法,即先报告,再讨论,大家举手赞成,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结果。”
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上的讲话,是对大会讨论的诚恳回应。中心思想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让群众有发言权,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犯了错误要进行自我批评,接受别人的批评。毛泽东还专门讲了刘邦、项羽争夺天下的故事,刘邦“虚心听取意见”,项羽“主观随意”,说明“刘邦胜利,项羽失败,不是偶然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带头为“大跃进”的错误承担领导责任,并进行了自我批评。
会议原定于1月30日结束,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延长会议时间,以便大家能在北京过春节(2月5日)。延长几天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说:“一个中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有些同志没有讲出来”,“在中央会议上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建议大家把气发泄出来,不发泄气就不能统一,没有民主就不能集中。因为不发泄气,怎么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呢?”这个建议显然有利于会议成果的落实。如果毛泽东只是发表讲话,宣布总结经验的工作做好了,地方领导人心里的结还是很难解开的,他们希望结合地方实际,把总结经验的工作做得更具体、更深入。 就这样,1月31日至2月7日的会议,主要内容是“泄愤”和“平怒”,即各省、市、区、部听取地县的意见,同时检讨过去几年的缺点和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引发会议争论的粮食统购问题,也不再纠结,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了统购任务,反对放权也逐渐淡出了会议的主题。这些做法,使与会人员平静下来,认为这次会议总结出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实体现。
有了活跃的民主气氛,大家的精神就畅通了,认识也统一了。接下来就是把吸取的经验教训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中去,克服困难。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提出:“要在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军事、政府、党等七个方面,总结经验,制定出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办法。”因为“光有总路线是不够的,还要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有适合于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军事、政府、党等各个方面情况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这样,才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以此为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七千人会议”前后制定和实施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特别是“七千人会议”以后,中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压缩“大跃进”时期盲目上马、投入巨大的一些项目,减少城镇人口,这些都是在当时认识条件下,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完善政策,并在实践中贯彻的重要举措。
这次会议原本是为了解决粮食统购问题而开的,原本是为了反对放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从中央到县级的领导,认识上有这么大的转变和提高,很了不起。今天的人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当时讨论的具体问题,但“七千人会议”召开的过程和方法,已经为后人积累了足够的启示,懂得如何处理问题,总结经验。
第一,解决问题,必须相互沟通,通过互动,找出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工作中,由于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对实际情况的理解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是常有的事。要找到解决办法,自然不能只着眼于具体现象,而要先找出背后的根源。要统一思想,必须避免主观武断,把结论强加于人。开会讨论,不是简单地让别人接受你的想法,应该鼓励大家讲真话,不要害怕分歧。只要讨论符合实际,改变会议原有的主题是可以的。只要充分发扬民主,就能“去偏向、归于一”,就能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
第二,总结经验,需要把遇到的实际问题具体化、深入分析,这样才能找到重点,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只是抽象笼统地讲,只讲原则上怎么样、基本上怎么样、一般怎么样,而不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总结出一些普遍的所谓经验,虽然很好,但不生动;虽然可能让大家高兴,但很可能是无效的或流于表面的,最终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在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达成共识之后,还要把解决问题的具体政策、措施和办法落实到位,并在实践中逐一落实。这样,总结经验才算真正全面有效。历史事实表明,“七千人会议”前后制定的各行业切实可行的具体工作条例,以及会议后对极不平衡的国民经济的有效调整,对扭转我国当时的严重困难局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早在1948年,在纠正土改中的偏向时,毛泽东就曾说过:“领导者的责任,不但要指出斗争的方向,确定斗争的任务,而且要总结具体的经验,迅速地推广到群众中,使正确的得以推广,错误的不再重演。”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在我们不断总结和运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
以上是我读完《变化:七千人会议的开始与结束》后的体会。
一本受到广泛关注的书,当然在不同人眼中会有不同的看法,以不同的方式激励读者,是其应有的效果。作者邀请我为这本新纪念版写序言,可能有点长,但我还是坚持把自己某一方面的经历完整地写出来,也算是用史实和材料表达了对严肃党史著作的应有的尊重。
(作者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原载于《中共新闻网》,经修改刊登;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