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收录平台【收录好,欢迎发文合作】发帖子的平台有哪些

尊敬的客户,您好!我们是北京一家专注互联网技术服务公司,可以提供收录效果好,文章排名好的网站进行发文,发得多,各种关键词排名就多,流量越多越稳定,如果您有需要欢迎您前来资讯!可以随意添加图文和视频广告,助您的企业或者项目服务实现推广效果!如需合作欢迎请加微信
下一篇文章内容预览:
如今,书评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批评形式,也是旁观者了解一本书好坏的重要渠道。但由于成本和理念等原因,大多数书评都是由作者或出版社编辑委托撰写,导致宠文堆积如山。中国书评人经常写宠文,一来是为了维护圈内关系,二来是迫于经济压力。由于书评稿酬不多,顶级文化媒体能给书评人开出每篇1000多元的稿酬(但能在其中发表文章的书评人寥寥无几),而大多数媒体给一篇书评的稿酬只有200到400元。一个书评人耐心地阅读一本新书,写出一篇经得起推敲的书评,收入却不如一个趁着热点的作家。因此,在今天,推广批判性书评,营造更好的阅读批评空间,改善书评人的经济状况,有着现实意义。 (本文首发于澎湃·中声专栏,作者授权转载)
图片:视觉中国
乾嘉学人钱大辛在《答西庄》中曾对王鸣声说:“学问,事关千秋,改过自新,不是批评前人,而是要造福后人。但批评必须公正、谦虚,一事一错,不影响大局,莫学宋儒‘一错,其余不值一看’之言。”[1]他主张批评要公正、适度,不能哗众取宠,不能卖弄个人感情。被批评的学者,不应该对批评心存怨恨,而应该自我反省。只有树立起良好的批评风气,才能更好地促进学术的发展。
钱大新的建议对于写书评很有帮助,他在评论别人的作品时,也恪守“公平讨论、语气谦和”的规范,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学者自身身份的认可。
在中国古代,书评并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书评。对于当时的知识阶层来说,书评与历史评论、朋友新写的诗篇或小说评论并无二致。《史记》中的“太史公说”是中国古代一种比较简单的书评形式。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虽然不是书评,但其文风和题材启发了后世学者创作书评。
明清时期,文人多以注解、阐释、评点的方式重温前人的作品。如人们熟知的金圣叹《水浒传》评点、李贽《西厢记》评点、脂砚斋《红楼梦》重注等,都是以这种形式来评论前人的作品。其中,金圣叹最为大胆,他不仅评点,还对原作进行修改,甚至将全书删除。例如,“他断定《水浒传》后五十回是罗贯中“加在尾部”的,便将其全部截去,声称自己得到了没有续篇的《观化堂古本》,并伪造了施耐庵序言,从而编造了今天流传的七十回本。他还断言《西厢记》第五回不是汪实甫所写,也是一篇“劣记”,便将其截去,以《梦醒时分》为结尾。”[2]
清末民初,现代书评文化逐渐传入中国,梁启超、李大钊、胡适等人利用自己的刊物、传媒资源,对外国著作进行介绍和评论,掀起了学者竞相写书评的风潮。
其中有像胡适《易卜生主义》那样的文章,从一本书中介绍一个人的文学思想和写作风格,也有像梁启超、李大钊那样的文笔,开合有致,犹如崩塌的岩石,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当时书评的语言文采和白话杂糅,书评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当时的世界正处于救亡启蒙时期,书评人大多关心时事、面向大众,有很强的责任感和发言欲望,对他们来说,书评就像是写好的演讲稿。
如今,书评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批评形式,也是旁观者了解一本书好坏的重要渠道。
在西方的学术评论体系中,书评的独立性受到高度重视。为了防止书评成为一项面子工程,西方书评体系一般有以下流程:“每个学术出版商出版一本学术专著之后,都要寄送到权威学术期刊。该期刊主编从中挑选出值得评论的书籍,邀请该专著研究领域的专家撰写书评。同时,也将书评寄给撰写书评的人。这种由期刊本身挑选权威专家的做法,有效地避免了作者或出版社主编将自己撰写或编辑的书寄给书评人的情况,因为后者必然会产生个人手稿。”(《荣新江:如何写好书评》)

但在中国,由于成本、观念等限制,大部分书评都是由作者或出版社编辑委托撰写,因此,受到青睐的书稿堆积如山。
中国的书评人写文章往往是求人情,一方面是为了圈内关系,另一方面是迫于经济压力。由于书评稿酬不高,顶级文化媒体能给书评人每篇稿酬超过1000元(但能刊登的却很少),多数媒体每篇稿酬只有200到400元。一个耐心看完新书、写出经得起推敲的书评的书评人,肯定不如一个利用热点的作家挣得多。
有时,他们发现,给别人写书评不仅很容易赚钱,而且很多媒体的编辑也接受这种做法(微妙的是,大多数媒体并不欢迎批判性的书评,而是把书评当成书籍简介,引述经典),从而降低了自己的写作道德。
同时,批评性的书评对出版商和媒体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学者荣新江在《如何写好书评》一文中指出:“在我国书评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一旦某位作者的书受到批评,有些人就可能利用这些书评来攻击作者,导致作者得不到职称,甚至影响到住房分配和加薪。有时候,再加上报纸、网站的炒作,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要知道,在西方杂志上,只有值得评论的书才会被安排评论,有的书根本就不值得评论。因此,即使书评中没有任何好话,也说明这本书不是最差的。”[3]
我经历过几次书评被拒。有一次,我写了一篇80后作家转型期小说的评论,投给某媒体编辑。编辑说写得不错,但领导的意思是不能说小说的坏话,于是书稿被退了回去。还有一次,一家出版社想再版余华的一本小说,让我写一篇书评。我对编辑说:“你可以写,但得允许我批评。”编辑答应了,但只暗示我批评的话,不要批评得太狠。两周后,我把书稿投了出去。结果,编辑和出版社的同事沟通后,通知我:“后半部分需要删除修改。”我问原因,编辑告诉我:“还是没有书评。”
大量偏袒性文章的出现,不仅破坏了严肃批评的氛围,也进一步挤压了批评性书评的空间。中国支持书评的媒体和刊物有限,有影响力的大型刊物屈指可数。偏袒性文章一旦占据大刊物版面,独立批评只能转向小刊物,但小刊物经营困难,依附大作家、大出版社的现象更加严重。很多地方小刊物早已沦为宣传阵地,不受欢迎的批评性文章更难脱颖而出。
久而久之,写软文就比批评更有价值,占据了更多版面,获得了更多话语权。作家甚至可以用软文来为自己的书籍铺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写批评不足以养活批评家。大多数批评家都有教职、学术身份或其他工作。如果写批评所能获得的微薄收入逐渐被软文蚕食,自制力不够的批评家必然会愤怒嫉妒,要么不批评,要么就去凑热闹。结果劣币驱逐良币,犀利的批评家越来越少了。
从自由到秩序:书评学术化的得与失
看到这种情况,有些人很怀念80年代的批评氛围。比如,李陀在接受查建英采访时回忆[4],80年代的批评很开放,朋友、学弟学妹都可以批评。年轻人敢对大作家说:“你写得不够好。”即使作家面色不悦,也会耐心听取同行的批评。但进入90年代后,这种氛围逐渐淡化,文坛上的人说话都比较谨慎,文坛逐渐变得权威有序。
八十年代的书评思潮比较开放,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批评家对西方现代理论的执迷、对大词的偏执以及批评家自身学术修养的不足都是客观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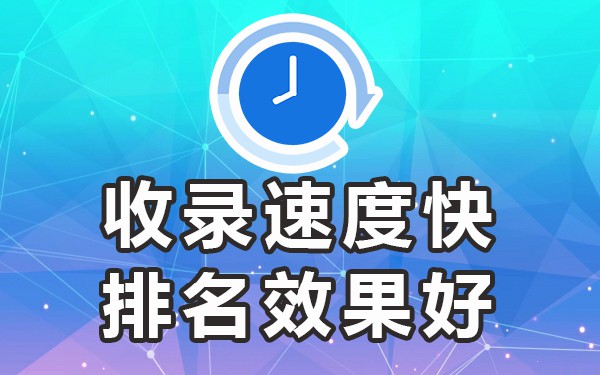
从专业知识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的书评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但作者的学术史视野却十分有限,常常拿起一些西方现代理论奉为珍宝,不加考证地将新理论套用到旧知识中。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福柯的规训、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等,都成为书评家乐于挥舞的棍棒,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书评文章往往上升到精神分析和权力规训的层面,但论证过程却十分牵强。
90年代以后,书评的专业性增强,书评人不再全盘接受西方知识,而是进入反思阶段,这对于书评的严谨性来说是一件好事。再加上国内出版物的规范化,严格地说,这二十年的书评质量比前一时期要高,涌现出了许多优秀文章,如周一良的《评冈崎文雄《魏晋南北朝通史》》(周一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数据整理——评杨子晖的《中国历代人口数据研究》》(葛剑雄、曹树基)、《歌曲中的复仇哲学——《铸剑》与《哈哈爱惜歌》关系解读》(高远东)。
相比较而言,80年代的书评顺应了当时的文化潮流,充满浪漫主义精神,渴望通过批评影响社会大众,因此,他们的措辞、句式更加通俗、时尚,注重批评的想象力和再创造性。
因此,刘福生在论述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时曾说:“批评家们虽然真诚地高举着人文主义、美学与形式的旗帜,但实际上却隐约意识到这些文学原则背后的政治解放的意义……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背后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乌托邦计划,它从这种社会历史动态中汲取了自己的文化主动性,以及将现实审美化、形式化的叙事能量。”[5]
90年代以后,书评经历了两次转向:一是变得更加学术化,风格更加学术化,就像写学术论文一样;二是变得更加大众化,将书评中的批判性元素去掉,变成简单的通俗读物。比如近几年流行的有声读物,其实就是这种书评的变种,以书稿为基础。
在这两种趋势下,书评逐渐丧失了创造性,成为古典话语的附属物。书评人制造的更多是“安全的解读”,而不是文学批评这种创造性的艺术。原本,创造性和批判精神是书评保持生命力的关键,但在今天的文化工业体系中,学院对秩序的崇尚和批判意识的缺乏培养,导致年轻的批评家很早就学会了冷淡的修辞,制造出理性、严谨、规范、平衡的“鉴赏文章”。这些文章格式规范,引经据典,如果仔细看,不会发现什么重大错误,但读者很难从中看到作者自己的创作——它们毫无攻击性,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充当古典理论的代言人。这种书评工作,成为既有古典判断标准和意识的重复。
作家卡尔维诺
经典书评《正确的废话》
因此,如今的书评里充斥着“正确的胡说八道”。作者用神秘深奥的理论来掩盖自己缺乏自我批评能力。结果,书评越来越疏远大众,成为一群人相互识别的工具。作者用这种方式确保同行能够认同自己。不同的语言和写作风格成为学者区别于他人的一种方式。立志成为职业批评家、成为权威的学者,自然会服从这种符合现代学术体系的语言标准。
这些批评的作者沉溺于教条式的解释,用现代学术规范来干预文本,把批评变成批评对象的小摆设,变成可以带入学术数据库的合格产品。这样的批评高度标准化,但其审美价值却极其有限,它们只是流水线上生产的零件,缺乏自己的风格和力量。以至于乔治·斯坦纳曾告诫批评家:“批评家如果对自己诚实,就会知道他的判断不会有长期的有效性,明天就可能被推翻。只有一件事能使他的作品具有某种永恒性:他实际风格的力量或美感。通过风格,批评可能反过来成为文学。”[6]

近一百年前,鲁迅在谈及“对批评家的希望”时说:“我所希望的,是他们要有点常识,知道裸体画和春宫画的区别,知道接吻和性交的区别,知道解剖尸体和残害尸体的区别,知道留学和‘放四夷’的区别,知道笋和竹子的区别软文网,知道猫和老虎的区别,知道老虎和洋馆子的区别,……”总之,批评家要掌握相关领域的常识,使自己的批评付诸实践,不至于成为空谈,这样才能做到“真批评”。[7]“真批评”不仅包括对文本的深刻阐释,而且要洞察批评对象与历史现实、社会现实的关系,开拓广阔的话语空间。
今天,与其说我们缺乏“真正的批评”,不如说在今天的批评中,真正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书评太少,带有学术口吻、安全生产说明的书评太多。书评的软文化已经成为现实,书评人的经济和地位劣势已无须细说。要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只能重拾批判性思维,对不愉快的批评更加宽容,不再将书评视为一种依赖,而是发掘其创造性的一面,支持那些敢于批评的作者,同时区分科普书评和软文。
毕竟,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批评。这是文化界的常识,但在常识稀缺的环境中,重申常识却成了一件罕见的事。
参考:
[1] 钱大新:《答汪希庄》,《千言堂散文集》第35卷,商务印书馆,民国(1912-1949)
[2]王静瑜,《金圣叹生平与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 荣新江:如何写好书评,明清史研究,2017
[4] 查建英:80年代的访谈,三联书店,2006-5
[5]刘福生:《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一个理论提纲》,《文学批评》2017年4月
[6] 乔治·施泰纳:《语言与沉默》,世纪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7]鲁迅: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